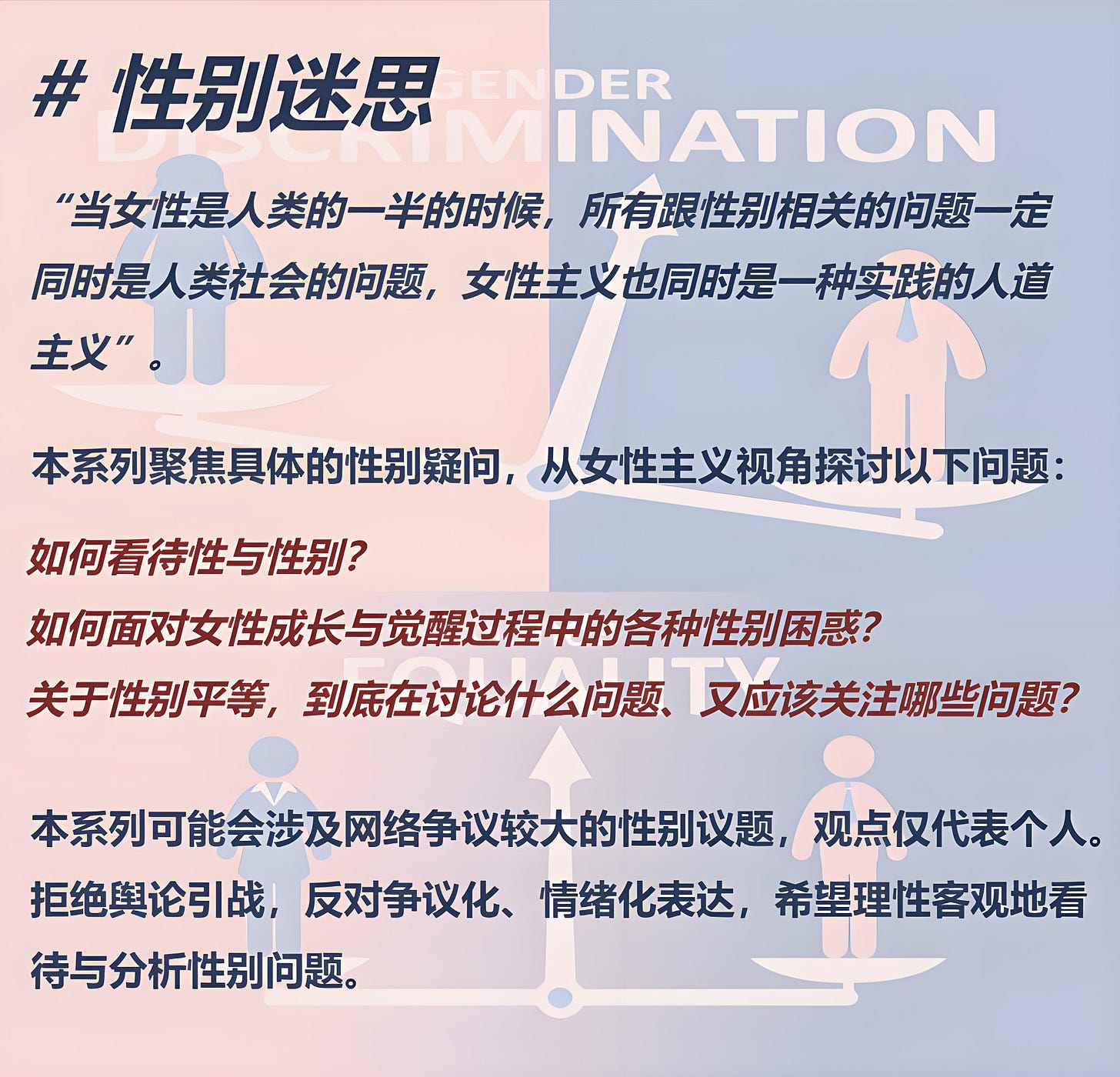性别迷思19| 对她的“双标指控”:既要彩礼,又要平等,是她在吃“女权自助餐”吗?
要不要彩礼,还真不是一个选择题
“你们这些小仙女一边嚷着要女男平等,一边又向男的伸手要彩礼、没房没车就不嫁,还真是双标!”
在现实生活中,女性面临的“双标指控”不胜枚举,对于“既要有要”的审判也层出不穷:
争取职场平等却默许约会买单的性别分工;
要求打破“玻璃天花板”却不愿服兵役、下矿井;
要求男性分担家务与育儿,却希望婆妈帮忙带孩子;
批判彩礼物化女性,结婚却房子、车子、票子缺一不可……部分男性甚至为这种看似是“女性占尽好处”的现象取了一个别名——“女权自助餐”,用来批判女性只愿享受权利而不愿承担责任。
然而,女性主义批判的就是定义权利与义务的父权框架本身。
只是,这部分男性所认为的“性别平等”其实是父权框架下的“性别均等”。
他们期待女性主义可以提供一套“完全对称”的解决方案——男人受的罪,你们女人也得受,不然就是在双标。
女性一边批判系统性压迫(如职场歧视、生育责任),一边迫于现实压力而妥协(如选择做全职主妇、接受彩礼)。
在他人眼中可能被解读为“说一套做一套”的双标,但实则反映出:在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的现实下,个体所作出的策略权衡。
上篇《对她的“驯化”:女性的性别特权,不就是皮鞭上抹万花油吗?》,我们了解了所谓女性“性别特权”的虚伪性。
本篇就以一直被视作“女性性别特权”的“彩礼”作为切口,呈现性别平等实践中的复杂肌理。
01 彩礼:压迫符号还是生存策略?
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面相
彩礼从周代“纳征”礼制演化而来,最初是农耕社会中女性作为“劳动力转移”的经济补偿(从父家转移到夫家),隐含将女性视为“可交易财产”的封建逻辑,其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物化的体现。
对于彩礼的传统解读,自然很容易进行批判。
而在当代社会,彩礼则呈现出两种复杂的异化形态:
在现代城市中,彩礼逐渐异化为“婚姻保证金”或阶层攀比符号。
从现实层面看,彩礼成为“资产重组”的一种手段,比如“有房减半彩礼”的隐形规则。
这也折射出现代婚姻市场的资本化倾向。而在大多数农村地区,彩礼仍是物化女性的历史逻辑的延续:
对女性生育价值的定价(江西“生男退半”潜规则) 、对女方家庭劳动力的买断(云南山区“彩礼抵弟媳”现象) 、对男性家族地位的确认(福建宗族社会中的“聘金公示制”)。
不仅如此,农村的高价彩礼更是成为“代际剥削”的工具,比如儿子的彩礼需要用嫁女儿男方给的彩礼作为资金填补。现实语境的复杂性
要求“彩礼平等”(彩礼与嫁妆价码相当),也不一定就意味着“公平”。
因为可能会忽略女性在婚姻中的隐性剥削(生育代价、职场歧视)。
倡导“不要彩礼”,也不一定能避免女性被物化。
比如,拒绝彩礼的城市女性面临“倒贴婚姻”的污名化(如被质疑“不配被重视”)。
更为现实的是,在社会保障薄弱(尤其农村地区),女性仍面临“从夫居”导致的原生家庭资源流失(比如农村女性因婚姻失去土地承包权、嫁妆用来贴补婆家用度)。
索要彩礼就成为一种“非自愿”但必须的生存策略了。
当城市女性用“不要彩礼”来彰显自我独立性时,请不要以精英视角审判那些不得不接受彩礼、求得生存的底层女性。
至于男性怎么想、怎么做,也不用在乎。
彩礼与平等的非对立性
在批判彩礼传统意义(物化女性)的基础上,思考彩礼的现代意义与现实功能,或许“要彩礼”与“要平等”也未必真的矛盾。
从现实补偿的角度来看,在现有社会结构下,女性仍承担更多无偿劳动(如家务、育儿)或面临职业发展限制。彩礼可视为对女性未来潜在牺牲的一种经济补偿。
从家庭资源再分配的角度来看,在部分地区,彩礼可能转化为新家庭的启动资金,或通过女方父母返还给小家庭(如嫁妆),从而形成双方家庭对新婚夫妇的支持。
02 “自助餐”指控:污名背后的权力博弈
在公共讨论中,“女权自助餐”常被用作消解女性正当诉求的工具,用个别案例否定系统性歧视(有人挥霍彩礼也不做家务),或是将结构性问题个体化(拜金女贪得无厌)。
彩礼被当成一种“性别红利”,位列男性定义的“女权自助餐”菜单之中。然而,彩礼作为“红利”这一前提本身就不成立。
彩礼之所以成为男性抨击女性吃“女权自助餐”的典型,是因为:
01 彩礼的货币化足够显性,人们很容易看到“钱是男方给的”、“给了多少钱”,却很难看到女性在家庭与婚姻中的隐形劳动、以及来自社会的对已婚女性的发展限制、各种歧视;
与其说彩礼是一种“红利”,不如说是入不敷出的些微补偿。
02 彩礼异化为阶层攀比的符号,彩礼的数额也在侧面反映男性的经济实力,而男性的经济能力又是个人成功的最直接体现,而个人成功又是父权脚本中早就写下的对男性的期望。
男性内化了父权成功学的逻辑,但这同样给许多男性造成巨大的心理和财务压力。
尤其对于那些经济地位下滑(或本就不占优势)的男性,他们若感到女性既要求平等又期待传统供养,便易产生极强的“被剥削”的怨愤情绪。而对“女权自助餐”的批评往往忽视一个关键事实:
所谓“女性逃避的责任”(如服兵役、从事高危工种),本身就是父权对“性别分工”的强制性定义;
而“女性享受的红利”(如彩礼)只是象征性的补偿。
要求女性“平等承担”这些责任,而未先解构其背后的性别暴力逻辑,实则是用平等口号延续压迫的结构。
当男性指责女性“既要彩礼又要平等”,实则回避了彩礼背后的结构性问题:
养老保障不足,农村女性需要通过彩礼争取未来的生存保障;
家务劳动的价值未被货币化,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付出被迫无偿化、义务化;
生育带来的身体损伤、职业发展受阻甚至中断,索要彩礼可能是对“母职惩罚”的风险对冲。从现实意义来看,女性收彩礼并不一定是违背性别平等的实践,而是制度缺位下的生存策略,更非单纯的“利己主义”。
女性主义的核心是赋予选择的自由,而非规定女性必须“完美抗争”。
要求女性在父权制未瓦解前就彻底拒绝所有传统实践(如彩礼),本质是新的道德绑架。
“女权自助餐”现象如同一面棱镜,折射出性别革命尚未完成的现实困境。它既暴露了个体在结构压迫下的局限性,也揭示了平等话语被工具化的风险。
03 谁在制造“自助餐”:个体选择与结构性压迫的矛盾
与其诘问谁吃“自助餐”,不如追究谁在制造“自助餐”。
结构性压迫的反弹
在长期性别不平等的环境中,女性被剥夺的权益形成巨大的历史债务。
当部分女性试图在现存制度框架内争取补偿时,可能不自觉地陷入“机会主义策略”——利用父权社会的既有规则(如“女士优先”、“男性应该买单”)作为谈判筹码。
这种策略本质上是弱势群体在权力不对等下的生存智慧,但也可能被异化为新的“特权”主张。
性别角色的碎片化转型
现代社会正处于传统性别秩序解构的过渡期:
公共领域呼吁打破“男性主导”(如职场平等);私人领域却保留“女性优势”(如婚恋中男性经济责任)。
这种割裂导致权利主张的“双重标准”,本质是旧秩序未完全瓦解、新秩序未充分建立的阶段性矛盾。
男性与女性都在适应性别角色转变的过程之中,难免存在新旧认知间的摩擦碰撞。
制度缺位的转嫁
丈夫本无义务供养妻子、提供彩礼,妻子也本无义务主力承担育儿及家务劳动。
是社会制度性保障的缺失,让男女被迫通过婚姻达成隐形交易,将社会责任分散到各个小家庭之中,将公共议题消解于两性博弈之中。
当社会无法提供普惠托育、平等就业与养老保障时,家庭就得被迫通过彩礼、房产等私人化等方案抵御风险。性别议题也成为了社会矛盾的替罪羊。
而在系统性压迫无法解决时,个体选择必然呈现矛盾性。
比如,城市白领女性既要求丈夫分担家务,又默许婆婆介入育儿。
比如,日本“平成新女性”既追求事业独立,又陷入“婚活”(结婚活动)焦虑。
再比如,“00后”在社交媒体上既批判“彩礼物化女性”,又要求男方提供婚房。
这些矛盾也恰恰证明,单纯的个人选择是无法替代制度性变革的。
资本与父权的合谋
消费主义将“女性独立”简化为“买买买”的自由,却忽视阶级差异。
底层女性既无资本享受“精致生活”,又因制度缺陷不得不依赖彩礼。
明明是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割裂,却被男性群体曲解为整个女性群体的“既要权利,又要特权”。
04 撕掉标签:从道德批判到制度重建
与其争论“(女性)该不该要彩礼”,不如追问:
如何通过土地确权保障农村女性财产独立?
如何建立普惠育儿体系减轻家庭负担?
如何立法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?
性别平等的实现,不在于苛责个体在破碎系统中的艰难抉择,而在于重建一个无需通过彩礼来补偿结构性不公的社会基础。
►解构彩礼的物化逻辑
破除彩礼对女性物化的逻辑,彩礼的意义与功能也可以与时俱进。
比如:将彩礼转化为“新婚夫妇创业基金”,重塑其功能;
建立“彩礼痛苦指数”,将婚俗改革纳入地方政府KPI考核。
再比如,江苏2023年试点“彩礼登记制”,超过当地人均收入3倍部分可追回,从而遏制买卖婚姻。
►解绑婚姻与生存
推动社会福利去家庭化(如单身生育保险、非婚同居权益),减少女性对婚姻的经济依赖,使其真正拥有“要或不要彩礼”的自由选择权。
►建立制度性补偿机制
针对历史性剥夺,不能停留于个体层面的“自助餐式”补偿,而需要建立法律和政策进行系统性纠偏:
01 反对针对育龄女性的职业歧视
产假、育儿假强制执行,且不能以怀孕、生育、哺乳为由拒绝女性应聘、上岗、晋升、涨薪等职业活动。
02 男性责任的制度化
强制男性休育儿假、推广“家务工资”等政策,打破“男性挣钱=履行义务”的单一模式,使平等成为可执行的制度而非道德呼吁。
比如,冰岛强制父亲休等量产假,否则取消家庭育儿补贴;日本2022年《促进男性育儿法》要求企业公布男性员工育儿假使用率 。
03 生育责任社会化
提供完善的社会性托管服务,且将生育、抚育子女的劳动“兑换”为实际价值。
比如,挪威的“性别平等养老金积分”,将抚育子女年限按比例折算为退休金;
法国的“生育贡献账户”,国家按生育次数直接向女性账户注资,切断与婚姻的经济绑定。或许大家都知道“如何做”、“怎样做最好”,可现实却是我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到。
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、社会福利制度、还是社会文化环境来看,我们都尚未具备上述制度建设的基础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接受不公平的性别秩序与性别分工、停下脚步、不做改变了。
恰恰相反,只要方向是正确的,就算道路曲折,我们也得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。
所有的变革都会经历阵痛,所有的未来也终将到来。
**************
要求女性在不公的系统性中做出“纯粹”的选择,就是制造“完美受害者”的逻辑。
无论作何选择,女性都是吃亏的一方。
关于“女权自助餐”争议,其本质是新旧性别秩序交替中的认知摩擦。
这也侧面反映出部分人对女性主义仍存在误解,同时也在警醒女性放弃“机会主义”的幻想,用父权规则是无法对抗父权的。
女性主义的目标不是审判个体是否“吃自助餐”,而是拆解制造饥饿的结构。
真正的平等并非零和博弈,而是打破压迫性结构,让两性都能摆脱传统角色的枷锁,“自由选择”才可能真正实现。
【性别迷思】,下期再见
下期“打直球”,聊一个女权定性话题——真假女权之辩。
与【第一人称她】永不失联:
Newsletter订阅链接:https://substack.com/@shecho(需科学/上网)
Medium主页链接: https://medium.com/@SHEcho.2025(需科学/上网)
微信公众号/知乎/小红书:搜索“第一人称她”
联系邮箱:shecho2025@126.com / shirleyhwang@proton.me(欢迎投稿来信及合作洽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