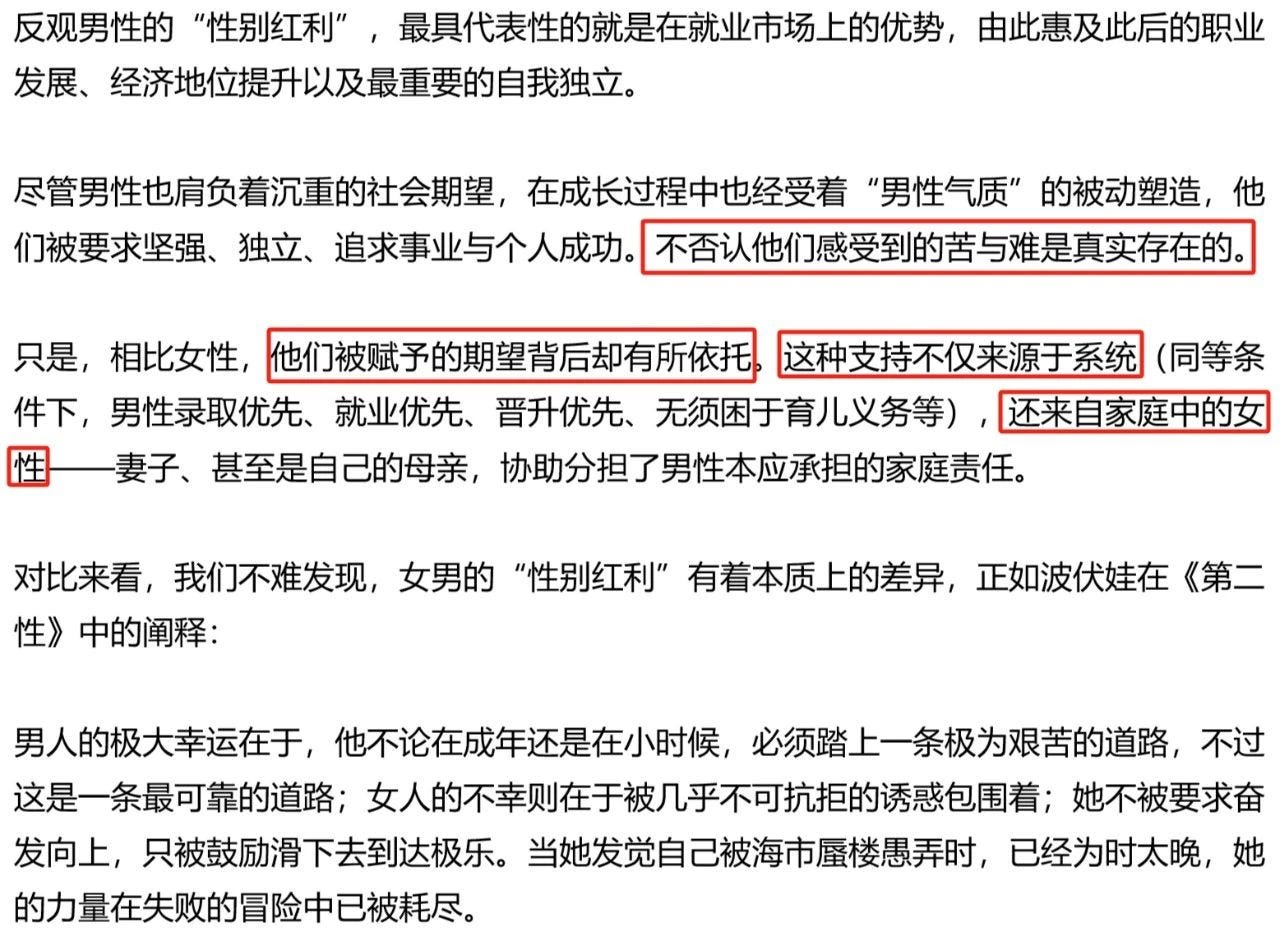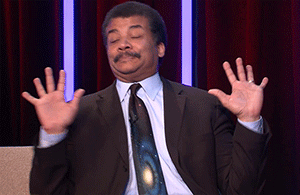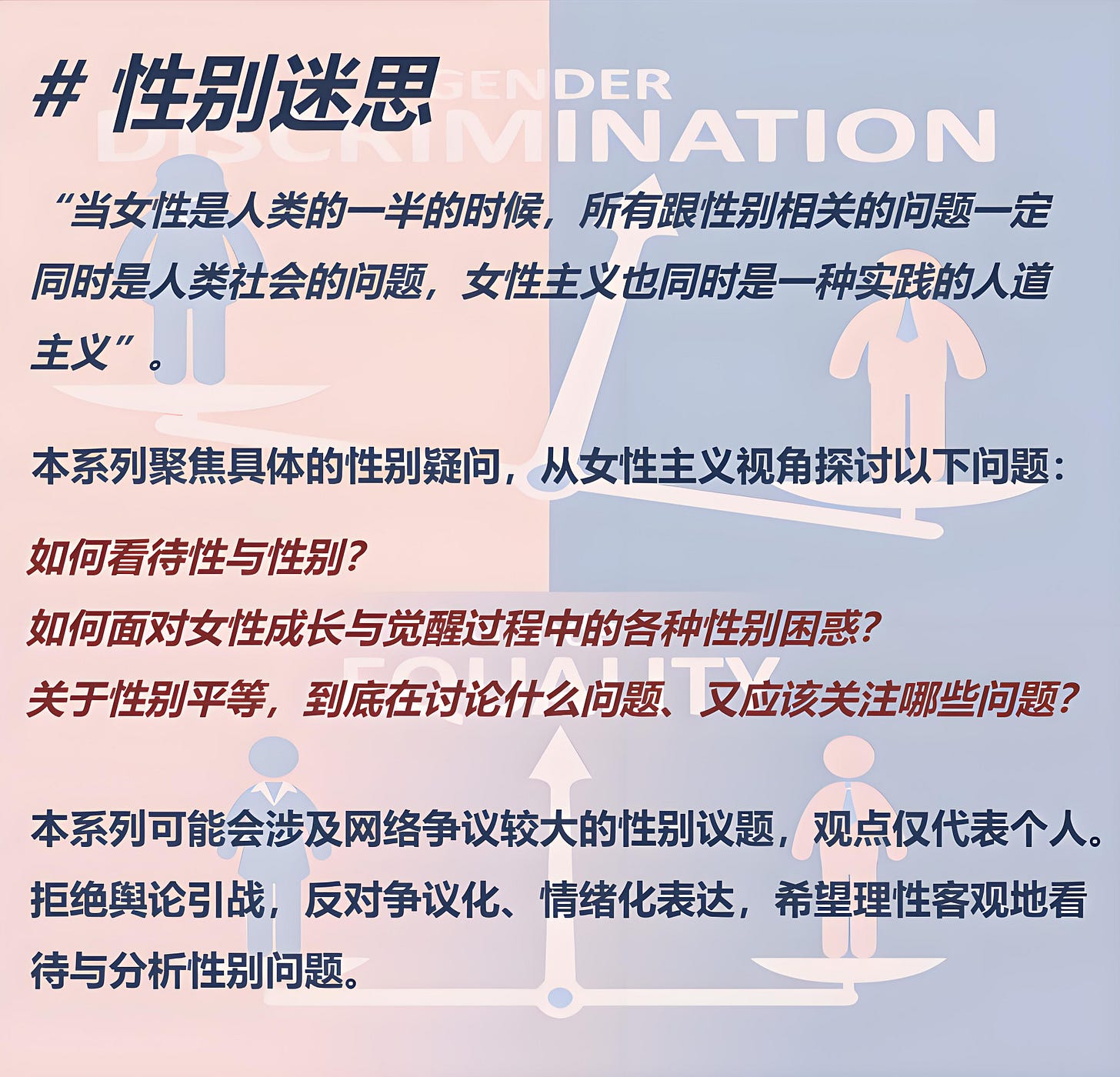性别迷思16| “不反抗,不合作”:4种视角,看男性为何沦为“父权代言人”?
一场与魔鬼的交易
【透视父权制】系列回顾:
01 《第一性的罪与罚:父权也会伤害自己的“好大儿”?》什么是父权制?
父权制如何对男性实施性别压迫?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男性同为父权制受害者这一身份?
02 如果针对男性的性别压迫确实存在,那又是什么在阻碍男性反抗?男性为何沦为父权代言人?
03 反抗父权压迫的男性,究竟是敌是友?他们正面临怎样的身份困境?女性又该以何种方式与态度作出回应?本篇汇总4类“父权代言人口号”,从不同视角探究在反父权压迫的具体行动中,男性不反抗、不合作的原因。
01 无意识的加害者:“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,女人也是”
无意识的受害人,往往也是无意识的加害者。意识到父权制的危害是“男性觉醒”的第一步。
如上一篇文章所阐述的,男性也深受父权制的限制与伤害。可是,如果男人们自己都无法认识到这点,就更别指望他们能理解女性的处境、一同反抗父权压迫。
这部分对父权伤害“无意识”的男性,恰好也是将父权期望完全内化,且认同既有性别秩序的一群人。
他们将男子气概与女性特质视作天经地义、将男性主导与女性顺从的角色期望当成理所当然、对不平等的两性地位与权力结构视若无睹。
他们得利而不自知、他们厌女而不自知、他们落入父权宏大叙事的陷阱中而不自知、他们既成为父权压迫女性的一环也不自知。
这类人既意识不到父权施加的伤害,也意识不到父权给予的特权。
因为“伤害”被扭曲为“为你好”,而特权的运作方式恰好就是“你有资格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”。
而这群人正是父权制得以继续宰制现代社会的根基。
他们既受到父权制的深刻影响,同时他们的存在又反过来维系并巩固了父权制所设定的性别结构。
02 成本收益分析:“父权制对男性利大于弊,净收益为正”
基于女性主义承认男性作为“父权制受害者与既得利益者”的双重身份,我们在思考“父权代言人”这件事上又多了一个新鲜的视角——权衡支持父权制的成本与收益。
将父权制与父权代言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某种“交易”关系:父权制提供“庇护”,父权代言人为此“上贡”。
当父权代言人在“庇护”下获得的实际收益超出了其“上贡”的代价时,他们便没有理由与父权制决裂。
引用《性别鸿沟的诞生:“她”和“他”为何渐行渐远、自说自话?》的阐述:
男性虽然挣扎于父权性别规范,他们无法自由地表达情感,还要承受自我实现与社会竞争的心理压力,但他们因为体制的“庇护”,在政治参与、教育、就业、医疗、文化乃至家庭等方面都享有切实的、优于女性的权益。
而且他们所享有的“性别红利”,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之上。
两者相权衡,“收益”确实大于“成本”。
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类男性:
他们清醒地知道男性的处境优于女性,也享受着男性身份带来的各种便利,甚至还会利用性别优势进一步压榨女性;
尽管他们也苦于僵化的性别规范,但为了维持父权制的种种好处,他们宁愿选择忍耐。
在我看来,这类男性的性质无异于“人贩子”:
通过“贩卖”女性获利,然后再将所得上贡一部分给默许“贩卖”的父权体制,体制反过来为男性创造更便利的“贩卖”制度与环境。
为了掩饰在不公平的性别秩序中作为“得利者”的心虚,他们还会无限放大自己作为“受害者”的一面,且尽可能弱化甚至否认作为“受益者”的身份。
这类“装睡”、“卖惨”的人往往最难团结与合作。因为他们的本质就是精致利己,在社会性框架中权衡算计,只为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。
03 权责对等:“男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,理应享受更多权利”
用“成本收益”的逻辑来理解父权代言人,更多出自女性视角。因为几乎很少有男性愿意承认作为“收益”的“性别特权”的存在。
男性更倾向于用“权责对等”的逻辑来合理化性别特权,将之变成一种既不用受批判、也不会心怀愧疚的“应得之物”。
“战场上死伤的军人是男性、矿井里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是男性、灾难救援时冲锋陷阵的是男性、承担养家糊口重担的是男性、买房买车付彩礼的是男性……”
因此,“男人比女人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,理应享受比女人更多的权利”。
这个逻辑乍看之下十分具有说服力,实则漏洞百出。
无论是战争、矿井、救援队、职场还是家庭,哪个场景中又没有女性呢?
战争中的女性被抹去、矿井中的女性被隐身、救援队中的女性被弱化、职场中的女性被歧视、家庭中的女性竭尽半生的付出被掩盖。
让男性上战场的是军事统治阶级而不是女性;
逼男性下矿井的是资本家(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阶级分化)而不是女性;
命男性主力救援的是灾情应对机构而不是女性;
让男性扮演供养者角色的是社会期望而不是女性;
让男性用物质换婚姻的是封建传统而不是女性。再往深一层思考,男性用“过重的责任”与“性别特权”的对冲,来合理化父权体制下不公平的性别利益分配,可他们很少去质疑这些责任本身的合理性、去对抗强加责任的对象。
就比如,不少男性会理直气壮地质问女性:
“你们凭什么宣称男女权利不平等?你们又没有承受男性的责任,有本事你也下矿、上战场、服兵役!”
然而,以战争为例,它本来就是统治阶级与军事领袖主导的不正义行径,男人也是战争与暴力的受害者。
男人们为何不去批判战争的无意义与统治阶级的残忍,而是要拉上女人一起被虐?
父权的诡计就是制造一个男女双方通过剥削彼此获得利益的假象,让男女互相仇视,而父权“坐收渔翁之利”,将两边都吃干抹净。
比如,女性看到的是男性在就业、薪酬、社会福利等方面更受优待,使得女性生存与发展空间备受挤压;
而男性看到的是女性可以通过婚姻(男人)拥有“更轻松的选择”、享受由男性创造的安全空间以及物质条件。
现实却是,父权联合资本主义,结合性别与阶级进行双重剥削:
一边剥削女性进行社会再生产,却不承认女性的价值、不予以应得之权益;
一边将在社会生产领域剥削女性所获得的“收益”与男性“分红”,从而进一步剥削男性劳动(尤其是底层男性)。
认同“权责对等”逻辑的这类男性,实则忽略了两性在父权结构中的“内生不平等性”——往一个本就倾斜的天平两端加同样的砝码,这种做法并不会让天平平衡。
04 个人主义的不作为:“我和那些男人不一样,但凭我一己之力也改变不了父权体制”
“父权制”显然不再只是一个束之高阁的学术名词,但大众对父权制的审视与批判似乎又过于肤浅——“哦,都是父权制的错”。
“父权制”仿佛只是性别战争中被人为树立起的靶子,一个充当转移炮火的工具而已。
这样的现象也着实令人迷惑:
既然父权制是人人口诛笔伐的“万恶之源”,它如同一头嗜血的巨兽,盘踞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之中、压迫着所有人;
那为什么问及解决方案时,父权制又总被当作无力撼动的背景板,被隐身、被忽略、被排除在变革对象之外呢?
一方面,个体可以通过强调体制与结构的【问题】,来弱化或回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。
“不是我的错,我也是受害者”:
在矛盾与冲突来袭时,受害者的身份可以让个体占领道德制高点,从而避免自己遭到攻击。
“都是父权的错,但我和父权没关系,我又没有歧视女性、也没有性骚扰女性”:
作为父权体系构建的重要参与者,男性就算主观想要与父权撇清关系,他们依旧改变不了自己身处其中、“助纣为虐”(哪怕是被动参与)的现实。“与我无关”是一种最小阻力、最低成本的自洽路径,即“维持现状、口头切割”。但同样也是最无助于动摇父权制的方式。
另一方面,个体可以通过强调体制与结构的【力量】,来合理化自己的“不作为”与“不敢作为”。
“凭我一己之力也无法改变”:
男性既在这种制度中享有特权,但又无力改变制度本身。
他们不想时刻被内疚与羞愧占领,便只能作出“体制凭个人之力难以撼动,就算我改变了,其他人不变,这个世界依旧不会变得更好”的摆烂言论。当每个人都抱以积极的绝望心态时,潜在的变革可能也会变得不可能。
因此,归咎父权制是最安全的选择。因为这坨“庞然大物”虽然无法被真正问责,但它也无法为自己辩解。
**************
男性不等同于父权,批判父权也并非意在否定所有男性。
父权制是一种权力运行的系统,批判父权是为了揭示性别压迫的根源。
女性主义并不是要责怪男性或让男性感到有罪感。相反,它邀请男性一起加入拆解父权制的工程,共同寻求解放和进步。
男人的敌人不是女人而是父权,对于女性也是如此。
如果一提到对父权的批判就跳脚,这类人或许应该先自我反思一下是否对父权制有很深的认同。
或许从上述几类视角中,可以找到自己沦为“父权代言人”的具体原因。
【性别迷思】,下期再见
下期我们聊聊“女权男”。
与【第一人称她】永不失联:
Newsletter订阅链接:https://substack.com/@shecho(需科学/上网)
Medium主页链接: https://medium.com/@SHEcho.2025(需科学/上网)
微信公众号/知乎/小红书:搜索“第一人称她”
联系邮箱:shecho2025@126.com / shirleyhwang@proton.me(欢迎投稿来信及合作洽谈)